编者按:
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自1956年创建以来,秉承校主陈嘉庚先生“独是师资一项,最为无上第一要切”的精神,始终坚持育人为先,爱生如子,在六十五载学院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教师,他们用毕生的奉献和爱心,践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用满腔热忱书写立德树人的动人篇章,为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6万多名各类专门人才,他们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中外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花。
值此建校百年和学院成立65周年之际,学院开设“学院荣光”系列专访,通过分享他们的故事,记录和追忆为学院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老师们,同时也展现学子风采,传递师生榜样力量,激发在校学子珍惜韶华、为院增光的斗志,进一步凝聚师生爱校荣校的共识,为新时代学院新发展汇聚精神力量。
个人简介:
潘懋元,1920年8月4日出生,广东揭阳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曾任厦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顾问、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等职位,他还是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历史上由海外函授部更名为海外函授学院时的首任院长;现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兼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等数十所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兼任或名誉教授、研究员、顾问。他曾参与组织编写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高等教育学》,还著有《潘懋元教育口述史》《高等教育学讲座》等等,且获得过“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当代教育名家”等诸多荣誉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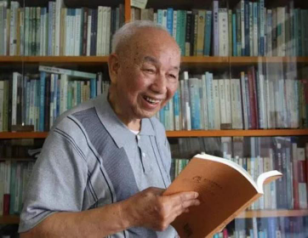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赤子之心,桃李天下

潘懋元(左二)与施蛰存(中)等师生合影留念
潘懋元先生从15岁开始从教,至今已八十八年,执教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其中担任了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大学教务处长、大学校长。他倾其一生奉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中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热爱教育工作、忠于教育事业。厦门大学有一个坚持多年的学术传统——周末学术沙龙,其首创者,正是潘懋元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潘懋元先生就在每周六晚上,邀请学生们到家中举行学术沙龙。沙龙举办时,潘懋元先生总是选择坐在门口,点燃一支烟,听弟子们的讨论。之所以选择坐在门口,是因为潘懋元信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允许学生与导师有不同的意见。“自由讨论,平等对话,启迪思维,追求真理”的沙龙学术原则,已成为厦门大学宝贵的学术传统。潘先生的学术沙龙迄今已举行了近800次,绝大多数参加过学术沙龙的人都深受启发,获益良多。正如我院2007级博士生、厦门大学档案馆馆长石慧霞写道,“沙龙使我把大学行政工作与学术思考结合起来,用思考的方式来看待工作和生活,用交流的方式达成精神自洽和和解共识。”
潘懋元先生曾深情地说:“我的理想就是当教师,当一个好老师”“我一生最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他怀抱一颗赤子之心,将三尺讲台视为人生之幸事,诠释了对教育这份事业的热情与奉献。他不仅在学术上勤奋钻研,更将“润物细无声”般的关爱毫无保留地给予了他的学生。1999年,厦门遭遇特强台风。台风过后,大雨滂沱,校园内一片狼藉,为了不耽误上课,已79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赤着脚、步履蹒跚地走进教室;一位学生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正在他为住宿费一筹莫展的时候,却被告知,潘懋元先生已替他垫上住宿费;一些家在外地的学生,逢寒暑假回家时,总会在第一时间接到潘懋元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询问路上是否顺利;有地方发生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潘懋元先生总是询问那里的学生是否平安;2000年80寿辰时,潘懋元先生从个人积蓄中拿出近20万元设立“懋元奖”,每年在厦大校庆期间对那些优秀年轻师生给予奖励。2006年,在厦大85周年校庆时,潘懋元先生又捐款25万元,其中20万元指定用于“懋元奖”,成为在校教师中个人捐款数额最大的一笔……从潘懋元先生身上的点点滴滴,学生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大爱,什么叫无私。
他培养的研究生成为知名学者、专家的近50人,已获得学位的硕士、博士百余名。在学生眼中,潘懋元不仅是一个导师,还是做人的航标。正如他自己常说的,“导师对学生在专业知识上的具体帮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点拨及人格上的影响。”
心系海院,兢兢业业 远见卓识,拨云见日

50年代初,东南亚地区教师大量匮乏,特别缺懂汉语的老师。1956年,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先生,确定了厦大的两个面向:一是面向海洋,二是面向东南亚华侨。
同年,厦大华侨函授部应时而生,为东南亚华侨培养语文及数理化专业方向的教师。当时报名学习人数众多,不仅有华侨,还有许多当地高中毕业生,因此华侨函授部后来更名为海外函授部。期间,因受文革影响,海外函授部停办,直到1980年开始恢复办学,正式更名为海外函授学院。从那时起,时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的潘懋元先生开始兼任海外函授学院首任院长。
他自己认为:“说我是首任院长,其实是很不称职的。海外函授学院及其后的海外教育学院,都是我的后任者和教师、职工们所做的贡献。”作为新建不久的学院,许多问题都会浮现。潘懋元先生公务繁忙,却仍旧心系海院,坚持每周都亲自前往学院,听取学院工作情况报告并给予恳切指导。我们可以发现,潘懋元先生不仅十分认真地对待学院事务,还给予了新兴学院精神上的强大凝聚力,作为海外函授学院的首任院长,如今的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能有目前的发展规模,他功不可没。
先生虽已离开学院多年,但始终心系海院,关心学院的发展。提及学院未来发展方向,先生多次强调要“走出去”。“海外教育学院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外国学生进来学习,更不能局限于基本汉语知识与中华文化的传播,更应当到外面办学,尤其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学。一带一路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广阔天地。”先生的思考让我们对于海外教育学院乃至学校的未来发展和差异化定位如拨云见日,心明眼亮。
瀚宇之花,香飘世界 文化传播,义不容辞

先生对青年一代“汉教人”也有着殷切希望,他认为我们“不要有大国架子,不能像某些国家搞优先主义,要从尊重他国文化到达互相尊重。”
尊重与共赢是我们新一代“汉教人”面对文化交流与冲突时应有的态度。我们要始终把合作共赢的理念、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把中国梦和世界梦的种子播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到它开花结果。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呼唤着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同放异彩、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力量,共同书写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篇章。
人生之路无坦途 走出困境天地宽

身为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们面临着许多关于专业、自身职业规划的难解之题。当我们虚心地向先生求教毕业季面临的就业困惑和烦恼时,他笑着对我们说:“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是我不害怕。15岁那年,我第一次给小学生上课,事先我花了很多心思备课,准备了很多材料,也制定了计划。可是到讲课那天,一上讲台就紧张得不知所措。结果才15分钟,就将备课的内容讲完了。学生们在下面叽叽喳喳、打打闹闹。为了教好书,我去读师范,想要掌握小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可是随后在给大学生们讲授教育学时又失败了,因为面对他们我仍旧照搬小学教育教学的方法,也因此受到了批评。这次失败让我把学习与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高等教育学,由此开启了我的高等教育研究道路。”
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潘懋元先生是厦门大学的教师,他敏锐地意识到,“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一样来教育”。面对中国无高等教育学科的窘状,他发出“大学生岂能像中学生、小学生一样教”之诘问。
1956年,暑假后的新学期,学生们发现,厦门大学的课程表里出现一个小小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变为了“高等学校教育学”。别看只是几字之差,却标志着“高等教育学”在我国首次作为独立的课程被搬上课堂。
10年动荡停下了潘懋元先生探索的脚步。直到1978年,《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两篇潘懋元先生的文章分别刊载于《光明日报》与《厦门大学学报》,振聋发聩,引人瞩目。有人如此评价潘懋元先生对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整个中国教育的贡献,“它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序幕,对后来以科学方法研究高等教育起到了启蒙和指导作用。”
1983年,《高等教育学讲座》出版,为第一本《高等教育学》的诞生和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4年,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出版,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诞生;1986年,厦门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潘懋元先生促成全国最早的4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
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不断试错的人生才是宝贵的、值得铭记的,面对失败,我们要吸取经验,永不放弃。我们本都是平凡人,而学会如何把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潘懋元先生身体力行地告诉了我们答案。“年轻人要敢于失败,面对失败”,这是先生对于新时代新青年的谆谆教诲。
文 | 洪钧 杨瑾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